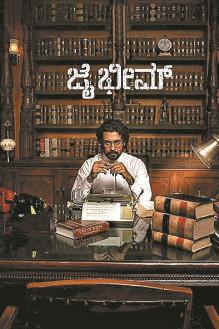
《杰伊·比姆》
《杰伊·比姆》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印度。为了提高破案率,营造高效的假象,警察经常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真正的罪犯是谁不重要,只要有人顶罪坐牢就万事大吉、结案盖棺。而顶罪人选当然是贱民们,他们身无分文,无依无靠,是最不起眼的小角色。很多被冤枉刚刚放出来的人,转眼就又被抓起来投入大牢。无需证据无需理由,只需严刑拷打到认罪服法即可。
拉贾坎努是一位平凡的老百姓,平日里努力工作养活老婆孩子,然而当地权贵家中的失窃案改写了拉贾坎努的命运,葬送了他的一生。权贵家中珠宝失窃后,失主首先怀疑的就是前几日来家中抓蛇的拉贾坎努。更重要的是,拉贾坎努是贱民。在权贵眼里,小偷小摸是贱民的天性。之后就是惨绝人寰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从印度教发源而来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代表着神话中原人的嘴到脚。除了四大等级,印度还存在着大量的“不可接触者”,意思就是“秽不可触”。这群“第五种姓”一度不被认可为印度人,只能从事最为卑微低贱的工作。虚无缥缈的种姓还象征着身份品质,低种姓自然而然被认为是道德败类。
时至今日,印度民间也没有彻底摒弃残忍的种姓制度。尽管法律中没有种姓规定,更明令禁止种姓的不公平对待,但蒙冤的“不可接触者”还是大有人在。早在1959年,印度宪法便明文规定“不可接触者”法律地位与一般公民相同,但腐朽的世俗观念并没得到改善,贱民依然是印度社会中被迫害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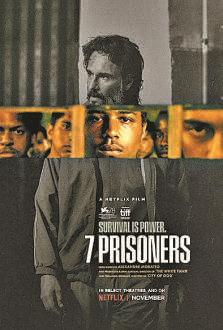
《七囚徒》
《七囚徒》一部巴西现代版的《包身工》。18岁的马图斯和镇上的其他少年一起辗转进城,到圣保罗工作。他们到了一个废品站,开始没日没夜地干活,工头卢克收走了他们的身份证和手机,并拳打脚踢威胁他们服从。本来大家一条心要逃跑,可是工头用利益分化了他们。
马图斯曾经策划逃跑,但是后来,已经跑出去的卷毛小黑被警察送了回来。劳动监管部门上门调查访谈,只要马图斯敢稍有异动,不但救不了自己,也会在卢克的信任测试中彻底失败。马图斯也曾经想铤而走险,杀了卢克后大家一起逃跑,但后来卢克带马图斯去见他的老板,老板是个有私人武装护卫,有权有势的议员。
马图斯最终选择做一个帮凶,“少年尚未屠龙,便成为了恶龙。”虽然他内心一直在挣扎,但终究还是选择与工头同流合污。曾经一起的小伙伴与他渐渐势不两立,但在他看来,别人的前途始终没有自己的人生重要。
受疫情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巴西2020年的GDP增长率从-5.3%下调为-9.1%,这可能是巴西120年以来面临的最大经济衰退。《七囚徒》这部张力十足的惊悚片,讲述的正是巴西经济衰退现状的黑暗面以及人们在其中求生般的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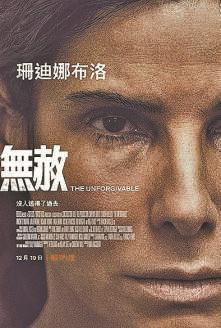
《无赦》
《无赦》一个因枪杀警长并为此获刑20年的女人露丝,假释后尝试与失散多年的亲人团聚。一贫如洗的她为了和亲人团聚仍不放弃任何机会,最终战胜重重阻拦如愿以偿。然而,所谓的“杀警黑历史”其实是影片抛出的一颗烟雾弹,真实情况是:单亲姐妹因为父亲自杀的关系,被政府上门送温暖要求托管,面临失去住所的风险。姐姐露丝必须拼尽全力和执法机关对峙,甚至都到了准备动刀动枪的地步。然而阴差阳错,彼时只有5岁的妹妹开枪打死了破门而入的警长,为了保护妹妹的未来,呵护一颗幼小的心灵,姐姐一人扛下了全部罪责。
由于“背负命案”,露丝为获得探视妹妹的权利,不得不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这些程序建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妹妹有获得新生的权利,但它亦无情剥夺了姐姐露丝作为直系亲属的探视权,让她饱受煎熬。
面对血浓于水的羁绊,机械的司法程序或许应该给执着的亲情与爱多一点信心和让步。法律执行者斩钉截铁地保护着公平正义的同时,也应该保留着对自己的审视,保留着真相被还原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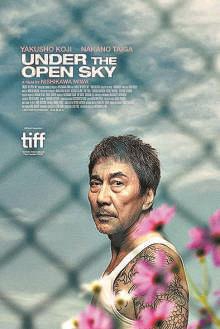
《美好的世界》
《美好的世界》展现的是一个并不美好的世界。一名前黑社会帮派分子因杀人罪被判入狱,在服刑13年后获释重返社会,发誓努力融入新的生活,然而当他被弹射到这个并不了解的新世界,根深蒂固的黑帮思维以及对有序社会体系语法的缺失,使他的生活反而越发变得与社会格格不入……一方面是经历监狱体系化改造重回社会的前重刑犯,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待这类人群的集体冷漠和无视。
电影根据佐木隆三的获奖小说《身份账》改编。所谓“身份账”,在片中特指一种用来记录犯人过往履历的记录本。这个记录本一般不对外公开,但男主三上正夫是个例外。他不但从狱方手中搞到了记载自己过往“光荣纪录”的身份簿,还打算出狱后,拿它登上电视节目,与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重聚。影片以极其冷静的视角,为观众剖析了一个平日鲜少关注的人群。
导演在谈到这部电影时说:“电影不应该只传递美好而愉悦的内容。社会上的受害者们,又或者是加害者们的故事也应该被写出来。我采访的故事可能是人们不想被公之于世的,或者看似毫无价值,但是我真心希望这样的电影能够成为人们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的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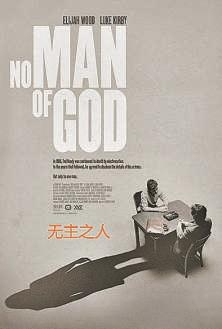
《无主之人》
《无主之人》:本片设定在一个单独的审讯室中,故事根据FBI心理分析师比尔·哈格迈尔与连环杀手泰德·邦迪于1984年至1989年之间的对话文字摘录改编。比尔·哈格迈尔连续访问泰德·邦迪的目的,是为FBI行为科学部犯罪心理侧写。导演特地回避了世人对心理变态杀手的猎奇,而是在作品中讨论了“人为什么作恶”这一主题,以一种人文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人类内心相同的黑暗和罪恶:他们是怎样被沉重十字的阴影覆盖,又是怎样作出不同的选择。
泰德·邦迪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连环杀手,围绕他的电影层出不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泰德·邦迪就是犯罪学家研究连环杀手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外表英俊、谈吐不凡——他是公认的高富帅,他从不缺乏外界的认同感。但与此同时,他是至少36起连环杀人案的始作俑者。他因在狱中协助警方分析另一起连环杀人案而被影片《沉默的羔羊》设定为人物原型之一。
比尔·哈格迈尔的童年并不幸福,但他仍旧成为“我孩子知道,他的爸爸是在保护大家”的人;泰德·邦迪却在成长过程中扭曲成为恶魔。究竟是谁造就了比尔·哈格迈尔,信仰还是他天生的正直与善良?又是什么把泰德·邦迪变成了魔鬼,是那个时代的影响又或者是他畸形的占有欲?电影的场景极为单调,就一间审讯室,全靠对白来推动人物。比尔·哈格迈尔与泰德·邦迪两人经过心理角力,多次较量之后,彼此熟悉与理解,最终有了近乎朋友一样的复杂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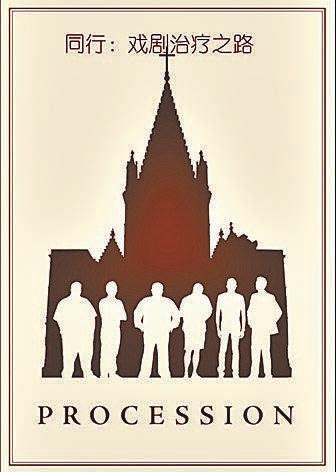
《同行:戏剧治疗之路》
《同行:戏剧治疗之路》:6名童年时被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的男子走到一起,开展一个受戏剧治疗启发的实验。他们根据记忆、梦境和经历创造了虚构的场景,意在探索教会的仪式、文化和等级制度,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导致他们在被虐待时无人吱声。
他们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多重的,是受害者、幸存者,也是别人的拯救者。重建并直接呈现于眼前的场景具有冲击性,虚构与现实的一线间隔随时被打破。这些勇敢的男孩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在颤抖着流泪之后依然选择继续;他们敢于向世界宣布,曾经被自己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那正是必须让人们知道的真相。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怜悯,也相互支持。疗愈的过程极度痛苦,让我们在观影过程中止不住一再质疑,这样直面痛苦到底对不对?
戏剧治疗在这个故事中并不是重点,它更像是一种打开过去的开关,引导着我们进入这些曾被教会荼毒过的男孩们隐秘的内心世界。戏剧疗法作为一种成本高昂、执行复杂的心理治疗范式,不过是为电影提供戏剧化的呈现。而心理创伤幸存者们的内心疗愈过程打动人心,才是电影所要呈现的内核。

《在糟糕的日子里》
《在糟糕的日子里》是一部挪威出品的黑色幽默电影,导演托米·维尔科拉延续了他在《死亡之雪》系列的恶趣味,讲述了一个另类婚姻故事。男主角拉斯是一名事业陷入低谷的导演,只能接到一些肥皂剧的小活儿;女主角丽莎是一名同样陷入困境的女演员,演技拙劣而不自知,最出名的角色是在男性广告中的角色。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拉斯和丽莎彼此厌恶憎恨对方,杀心顿起,恨不得对方立刻暴毙,自己独得几百万人身意外险。原本相亲相爱走到一起的两个人,如今变得恨不得弄死对方。
导演托米·维尔科拉的处女作《杀死比利》致敬了经典影片《杀死比尔》,并且同样拍了两部,还获得了昆汀本人的夸赞。虽然恶趣味十足,但却暴露了他的Cult片迷的身份,并且奠定了他后来的创作基调。Cult电影即Cult film或Cult Movie,指拍摄手法独特、题材诡异、风格异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富有争议性,通常是低成本制作,不以市场为主导的影片。它的特点是类型多元化:暴力片、科幻片、恐怖片、黑色喜剧、西部片、实验电影等等各种标榜着另类和决不妥协口号的电影,都可以称为Cult电影,常常是科幻、恐怖、音乐、动画、喜剧的大杂烩。《在糟糕的日子里》虽然是Cult片风格,但它在“娱乐”的外表下直指婚姻中的致命问题,让人悚然并反思。

《米沙与狼》
《米沙与狼》揭示了一个虚假的故事:她是纳粹迫害之下的犹太孤儿,也是独自穿越千里丛林的勇敢女孩,她在丛林中与凶恶的野狼为伴。1997年,米沙据此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与狼共存》,引发轰动,许多读者都被书中催人泪下的传奇故事深深震撼。2007年2月,由法国、比利时拍摄的同名电影《与狼共存》引发观影热潮,至今依然在“优秀电影”之列。
然而在与出版社编辑的经济纠纷中,米沙的贪得无厌令合作多年的编辑身败名裂。不知是存心报复还是无心插柳,编辑发现了米沙回忆录中的漏洞,最后从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抽丝剥茧,发现了米沙惊人的秘密。此后,米沙在接受一家比利时媒体采访时出人意料地宣布,她根本不是犹太人,自传中所谓“与狼共存”的那段时间里,她还只是一个4岁女孩,回忆录“纯属虚构”,书中那些传奇经历全是她编造的。
原来不仅所谓“孤女、丛林、野狼”的故事并不存在,甚至米沙被迫害的犹太人后裔的身份都是假的,无数人为之感动的故事竟然全部来自米沙的杜撰。原来,米沙的父亲曾被骂作叛国贼,而米沙极有可能出于逃避“卖国贼之女”身份的想法,给自己“塑造”了一个战争受害者的身份。长时间的自欺欺人更可能让米沙的精神状态彻底改变,所以她才能在无数次的访谈中“真情实感”地谈论战争和伤痛,感动了无数人。







